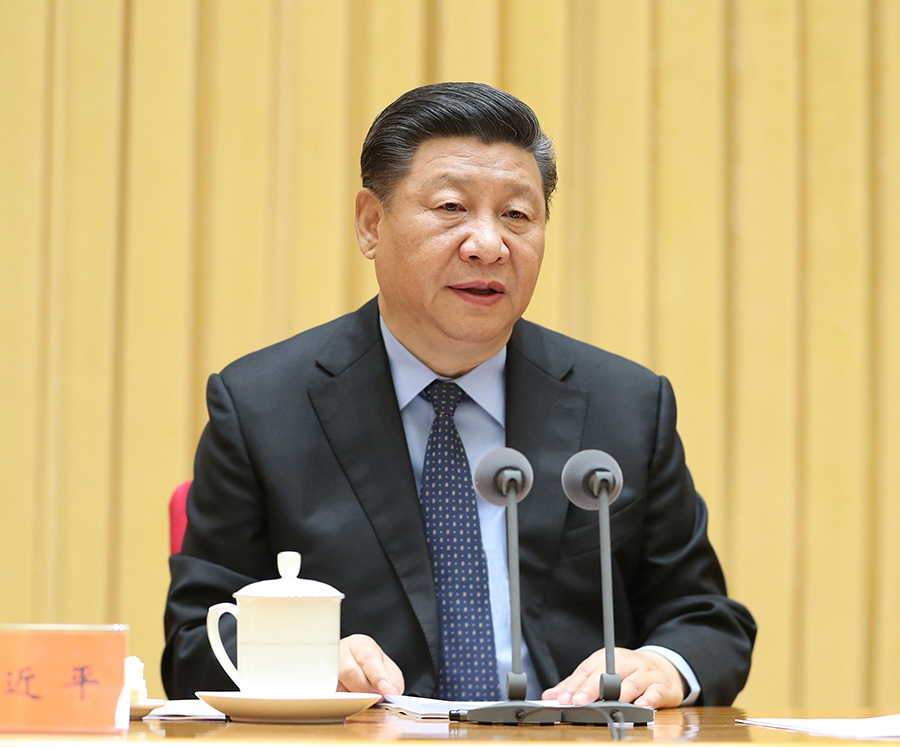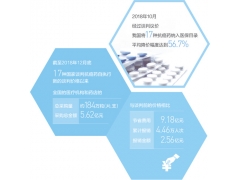新华社记者
这个夏季,是41岁的帕米尔牧羊人库瓦提·萨热在“铁日孜窝孜”牧场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季。明年,他将告别祖辈延续了上千年的高原游牧生活,在平原定居。
像将要发生在库瓦提·萨热身上的变化一样,到2020年,世代游牧于帕米尔高原深山牧场的数万柯尔克孜族贫困牧民,都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,走出深山,定居平原,结束延续了千年的游牧生活。
库瓦提·萨热是新疆阿克陶县克孜勒陶乡喀拉塔什其木干村牧民。他夏季放牧的“铁日孜窝孜”牧场,海拔4100米,柯尔克孜语意思是“难觅之境”。
“铁日孜窝孜”牧场虽距村委会不到30公里,牧道上却巨石密布,崎岖难行,很多地方一面紧贴山崖,一面就是深涧激流,最窄之处不到1尺,人畜跌下悬崖的惨剧几乎每年都发生。
为了在亘古高原给牛羊寻觅足够多的饲草,并保证草场不会被牛羊过度啃食导致退化,每年,这里的牧羊人都要骑着马和毛驴,带着全部家当,赶着牛羊,翻山越岭,四处转场。
库瓦提·萨热的转场之路,是古丝绸之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必经通道之一。以前,这里的牧人就曾用骆驼、马和牦牛,为往来商队驮运布匹、茶叶、丝绸等货物,赚取报酬补贴家用。然而,守着贸易通道,上千年来这里的牧羊人却始终没能摆脱贫困。
不通路、不通电、不通网、没有通信信号,像“铁日孜窝孜”夏牧场一样,喀喇昆仑山的重重山脉,将不少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居住点切割成碎片,撒在沟壑深谷间,阻断了交通,也阻断了发展。
这里,拥有牲畜的数量决定财富的多寡,然而,瘠薄的高山草场却无法养活太多牲畜,一旦遭遇天灾,牧民家就要揭不开锅。
库瓦提·萨热11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羊鞭,20岁结婚时,从父亲手中分到30只羊。可21年过去,他的羊仍旧是30只。
“这些年,人越来越多,草越来越差,羊好不容易增加了几只,但家人生场大病就只得贱卖救急,再遇个雪灾,几年血汗转眼就没了,养羊的人挣不上钱也吃不起羊啊。”库瓦提·萨热无奈地说。
几年前,阿克陶县实施集中办学,喀拉塔什其木干村的孩子们就成了“候鸟”,只在寒暑假回来。村子也成了“留守村”,留守的却是青壮年,“飞走”的是老人和孩子。被牛羊困住的男人们,既丢不开“饭碗”,又不敢外出“闯荡”。
库瓦提·萨热只能把摆脱贫困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2015年,他把7岁的小儿子加尔肯那勒·库瓦提送到乡小学寄宿读书。自那以后,夫妻俩每周都要赶两天山路去村委会给儿子打电话。
甚至,暑假孩子想学柯尔克孜族传统的叼羊和赛马技术,都被库瓦提·萨热拒绝了。他觉得只有学好了知识,走下高原才能改变命运。“我只能放一辈子羊了,可孩子得有新的生活。”库瓦提·萨热说。
南疆四地州是国家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,贫困程度深,而帕米尔高原则是南疆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这里海拔高、条件艰苦、自然环境恶劣、自然灾害频发,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难度极大。因此,易地扶贫搬迁,成了改变帕米尔高原牧民生活的可行路径。
去年,搬迁方案传到“铁日孜窝孜”夏牧场后,得到了全体牧民的支持。村民大会讨论,决定让牛羊少和有老人的家庭先搬迁,年轻力壮的后期再分批搬迁下山。牧民迁至阿克陶县城郊平原地带后,当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免费住所和蔬菜大棚,并通过劳务输出、就地就业等帮助牧民增收致富,最终只留少数人固边守土,为大伙儿“代牧”。“高原恶劣的环境我们都能生存下来,下山重新开始完全不同的生活,我们一定能慢慢适应。”牧民买买提·霍加说。
对于搬迁这个突然而至的变化,60岁的牧羊人吐尔地库力·米曼感到欣喜。他说:“年轻时,夏牧场的草能长到大腿根子,可现在,很多地方像‘谢了顶的秃子’,长势好的草也只到脚脖子,再这么下去,草场就要完了,草场给了我们一切,也该让它歇歇了。”
喀拉塔什其木干村“更新换代”的年轻人,再也没有“故土难离”的想法。刚考上大学的买买提阿克木·阿不都热扎克说:“大学毕业后,我要想办法留在城里工作,过上更好的生活,不能再让大山困住我们的脚步。”(记者 阿依努尔、宿传义、江文耀、冯太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