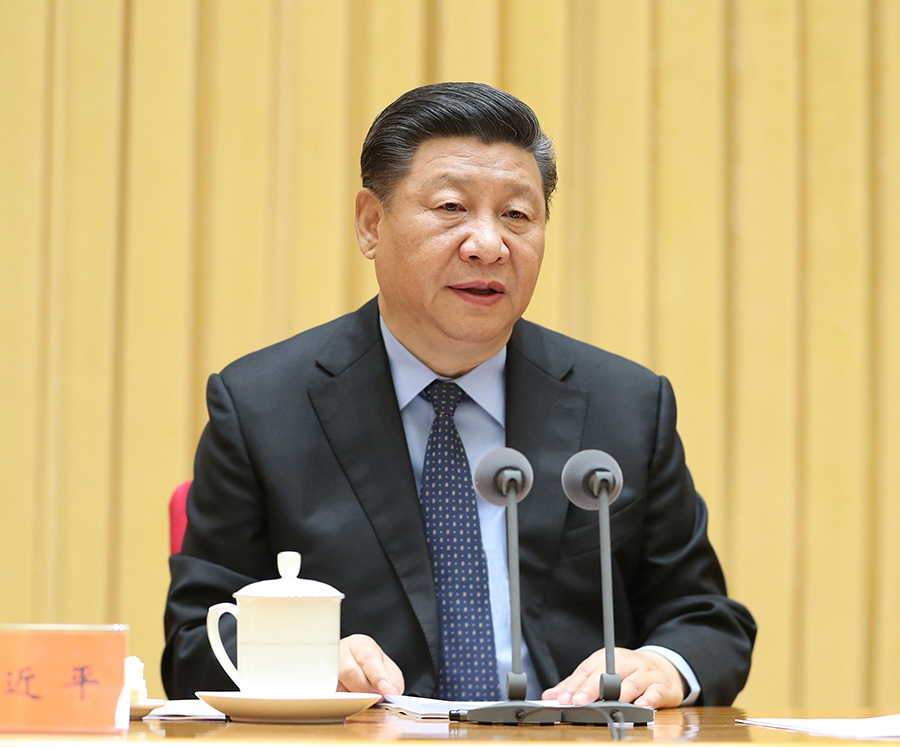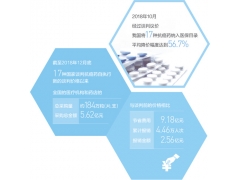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效之关键在于人口流动,而决定人口流动的因素却不只是户籍制度。
人口流动对经济的影响既表现为供给侧,又表现为需求侧。供给侧而言,人口自由流动是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表现,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的转移,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;需求侧而言,人口流动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收入,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,这都将提升有效需求。所以,人口流动对宏观经济整体而言是有利的,但人口流动与否却取决于微观主体的选择。
从微观个体的经济动机而言,迁移与否需要做成本收益分析。哈里斯-托达罗(Harris-Todaro)模型认为引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是报酬的差异,所谓“人往高处走”,很多时候体现的就是对高工资的追求,因为它象征着更好的工作、福利和幸福指数。用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来说,劳动力流动是追求福利(或效用)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人的自发选择。但是,如果将个人行为扩大到家庭行为,考虑家庭总体福利最大化,部分行为人的行为可能就会发生变化。北京师范大学李实和邢春冰的研究显示,收入差异并非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唯一因素,公共服务、福利保障,以及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社会、适应当地习俗等都会影响到劳动力的迁移意愿。
放宽户籍制度的限制,有助于降低非户籍人口在城镇生活的成本,从而有助于吸引更多人口流向城市。但是,这里存在一个宏观经济学中常说的“合成谬误”,即个人理性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。具体而言,户籍制度改革的供给侧效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,而短期内,其对地产需求的拉动会更加明显,这又会反作用于供给侧,对供给侧形成挤出。因为房价上涨与劳动力供给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是相违背的。逻辑很简单,房价上涨利于有房者,他们是城市的存量劳动力。但房价上涨不利于城市新增劳动力,而他们才是供给侧的边际贡献者。房价上涨会增加潜在的新增劳动者的生活成本,必然成为阻碍其流向城市的因素。
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蹴而就,如果从1984年开始算起的话,至今已经有35年时间,但城乡户籍的区别仍然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。由于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,以及过去35年改革的缓慢推进,致使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大为下降。
不仅如此,户籍制度改革还需要一系列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比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,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,农村集体土地需要首先征收为国有土地才能入市,而农民从中所获得的土地收益非常低,卖地的大部分收入归政府。如果农民可以分享更大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,也将为他们在城镇置业提供资金支持,不至于面临当前这种“进不来,退不出”的两难境地。再比如教育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等,在当前城镇的公立教育和医疗供给已经短缺的情况下,户籍人口的增加又会增加公共服务的压力,从而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,这又需要推动财政体制的改革。所以,户籍制度改革也将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。
户籍制度改革,需要的是真金白银。一般而言,“畅销”城市财政状况好,有钱改,但仍然限制最多;而“滞销”城市,没钱改,即使限制取消了,也难以改变人口净流出的状况;对于有些“畅销”但没钱的城市,又得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。
总而言之,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,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“缓兵之计”,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“通行证”,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。但是,政策意图的实现,还需要其他配套政策(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、住房制度改革等)的配合。为了防止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成本迅速上升,决策层需要从劳动者的微观角度出发,进行成本收益核算,这样才有助于激励奏效。
(作者邵宇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)